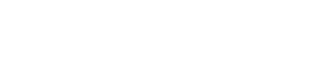研究背景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非数字原生企业而言,在转型过程中承受着比数字原生企业更大的压力和阻力。非数字原生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源于现代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之间的差异,更源于数字化转型这种组织变革活动对企业原有组织身份的冲击以及组织成员对新组织身份的困惑。组织身份构成了组织成员对组织使命、价值、资源、能力与产业结构的理解与感知,数字化转型困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组织成员对原有组织身份的坚守和对新组织身份的不适应,以及随之而来的组织身份冲突问题。作为一种组织变革活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划与推进方向在转型效果实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数字原生企业应如何选择数字化转型策略?哪种转型策略更有利于非数字原生企业克服原有组织身份的阻碍、更有利于有效达成数字化转型目标?这些成为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
刘淑春、李杨、潘李鹏和林汉川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5年第4期的论文《转型策略选择与非数字原生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组织身份冲突视角》基于中国首个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连续8年的企业动态调研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评估了非数字原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效果,进而实证检验了不同数字化转型策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效果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对非数字原生企业而言,自上而下的转型策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自下而上的转型策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转型策略可以通过有效促进组织成员间的知识流动、统一意义达成和提供职位安全保障三重机制,降低转型前后组织身份间三对冲突的负面影响,助力企业实现组织身份跃迁和转型。 第二,能否有效缓解非数字原生企业关于“专注稳定还是拥抱创新”“依赖内部资源还是链接外部资源”“习惯复杂性还是追求简洁性”这三对组织身份冲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影响数字化转型效果的关键环节。绩效压力会与自上而下转型策略一起形成“高要求—低控制”的工作环境,引发员工对新组织身份的负面情绪和抵抗心理,削弱自上而下的策略的正向作用;与之相反,绩效压力与自下而上的转型策略能形成“高要求—高控制”的作用环境,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有效调动,此时绩效压力成为一种激励因素,进而削弱了自下而上的转型策略的负向影响。另外,转型收益预期会强化自上而下的策略的正向作用。较高的收益预期通过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进而强化了自上而下的转型策略在缓解组织身份冲突上的作用。 第三,创业导向弱的企业与低制造业收入增速地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经历更为激烈的组织身份冲突,因而转型策略选择对其转型效果影响更为显著;而创业导向强的企业与高制造业收入增速地区企业因组织成员秉持勇于开拓的创业文化和拥有更多就业选择,反而经历较少的转型身份冲突,转型策略选择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启示 第一,强化“一把手工程”效应,构建自上而下推进的数字化转型策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的数字技术应用,而是要通过数字技术对企业的管理组织架构、价值创造方式和组织身份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变革。这一系列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推动非数字原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通过“一把手工程”构建自上而下的转型策略,尽力克服组织内部的思想阻力、组织身份冲突和路径依赖,对企业管理架构、组织体系、变革理念进行系统性重塑。 第二,引导企业选择与企业经营状况相匹配的转型策略,提振员工“数转”动力和信心。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的选择应当充分考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只有在业绩良好的条件下采取自上而下的转型策略,才能有利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效果。从转型收益预期来看,良好的预期能够有效提振企业家和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减少两种组织身份冲突对转型的干扰。这说明,面对转型挑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重视预期管理。 第三,充分考量各类异质性因素和差异化需求,完善企业数字化变革激励政策。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应当因企而异,改变政策面的“一刀切”和“大水漫灌”现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扶持从“漫灌”转向“滴灌”,结合创业导向、制造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定更为精准的激励政策,采用个性化的“量体裁衣”,推动企业立足其发展阶段形成差异化的转型模式,充分调动企业内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避坑防险、少走弯路、不走回头路。